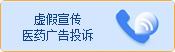月光是何时漫进来的?他竟浑然未觉。整个书房已浸在银白的雾霭之中,书案上的砚台泛着幽微水光,镇纸下的诗稿边缘也悄然发亮。他摊开手掌,见月光在指隙间静静流淌,恍惚间,竟觉得自己也化作了月光淬炼的一部分……作家戴志刚的散文集《月光皎白》,正是由无数个月光漫漶的夜晚堆叠而成。捧读这本尚带墨香的新书,字里行间仿佛浮现出作家清晰的侧影。
中国文人对月亮的独特情怀,大抵源自血脉里流淌千年的乡愁,那轮玉盘承载着世代文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故园情思。《月光皎白》上辑名为《人间有情》,戴志刚的思绪不断触及故土临澧,一股敬畏的寒意油然自脊背升起。恍若时光倒流,我们隔着三十余载的烟波,与童年的作家打了个照面。他裤兜里盛满了炒熟的北瓜子,边走边像只小老鼠般磕着,嚼碎了懵懂心事,也磨碎了悠悠光阴。
作家笔下的亲情,浸润着生命最温暖的底色。《嗲嗲》中的主角一辈子挺直腰杆做人,不仰人鼻息,不随波逐流,俨然是荒漠中一株离群索居的胡杨,千年孤独,万年苍凉。嗲嗲的爱无声无息,每每刮风下雨,甚至只是天色稍阴,作家总能在林中“巧遇”这位“随便转转”的老人。又如,母亲常叮嘱,人立于世当积德行善,她总虔诚祈祷神灵护佑后人无灾无妄。这般看似迷信的举动,曾遭年少的“我”暗自嗤笑。直到母亲如秋叶般飘落在素白的病榻上,那个鬓角已染霜华的中年儿子,才终于得以在输液管缠绕的床畔,将母亲枯枝般的手贴向自己温热的脸颊。刹那间,他读懂了母亲浑浊眼眸中,那些沉积了半个世纪、比叹息更轻的絮语。
湘西北乡人言语粗放,却浸透着山野的率真,善良淳朴是其唯一底色。脾性暴烈、连自家名字都难得写拢的德爷爷,却被作家定义为“最聪明的人”,他以惊人的智慧带领全家熬过苦难岁月;打心眼里疼爱孩童与小动物的春叔,总把猫碗狗钵洗得锃亮,归置灶头,从不随意踢放角落;还有偏不信邪、越老越犟的海爷,面若银盘、步履生风的丫姐,乃至榨茶籽时节,那些默默扛抬蛇皮袋、过秤、炒籽、压饼的父老乡亲……那些淳朴温暖的乡情,如同不熄的炉火,始终熨帖着戴志刚的童年。
然而,我们终究低估了时光的残忍。当那些鲜活的名字一个个随风飘散,一种酸楚骤然弥漫全身。作家对死亡隐忍的痛楚,恰如经年顽疾。作家不禁喟叹:当某天你永远失去了这个人,便如同一棵树被连根拔起。再忆及那些已然逝去的身影,宛如清晨立于树下,一串冰凉露珠自叶尖坠下,悄然滴落颈间。
《月光皎白》中的月光意象,堪称整部文集最为玄妙的精神图腾——它如雾霭般朦胧难辨,却又似晨露般晶莹剔透。透过文字织就的锦绣,我们触摸到了生命最深邃的脉动。天人永隔的锥心之痛,在每一个细胞里冲撞奔突。然而,死亡如同海浪的推涌,是生命延续的必然,非人力可阻;亦如山间茅草,岁岁枯荣。人终难逃尘归尘、土归土的宿命,一切终将交还给至公的大自然。
下辑《大地有痕》与上辑迥然相异,笔致流转间颇具余秋雨先生文化散文的气象,于厚重处见灵性,在沧桑中显隽永。戴志刚深谙古典文学精髓,千年文脉如璀璨星河,在其笔端自如流转。此辑讲述了诸多隐于泥土与时光深处的故事,刻录下作家生命旅程中一个个重要的精神驿站。
书中,我们与无数璀璨的灵魂不期而遇:宋玉、蔡伦、杜甫、范仲淹、刘禹锡、周敦颐、林则徐、林伯渠、史铁生……“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吞吐天地的气象铸就了湖湘文化傲然挺立的精神脊梁。每逢存亡之秋,无论达官显贵抑或贩夫走卒,从未偏安一隅、独善其身;循着周立波与丁玲的文学足迹,我们窥见两个文学村庄的时代交集,感受到潇湘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创造力;闭目遐思,澧阳平原肥沃温软的泥土气息拂面而来,数千年前城头山先民躬耕劳作的画卷徐徐展开——汗珠坠入泥土的脆响,耒耜翻动大地的韵律。
每个人的心底都驻着一方生命的原乡,戴志刚的心魂总为潇湘的云水烟岚而微微颤栗。《永州慢》里,我们随作家体味柳宗元笔下山水那固有而独特的节奏,见证了永州人骨子里的谦逊与独立。当我们在潇湘之源的永州柳子祠与先贤对话时,便豁然领悟:做事不可半途而废,为文不可浅尝辄止。人生之道,贵在深耕厚植,不囿于一得之功。人生何其短暂,不过数十寒暑,多少光阴虚掷于无谓之事,可悲亦可叹。
戴志刚骨子里的浪漫与不羁,将生命的本真映照得澄澈通透。《月光皎白》道出了我们习焉不察的生命真谛:世间诸多事理,本就如云烟般缥缈,或本无答案,或不必追问。月光大抵蕴着魔力,那清泠的银辉,总令人不自觉地卸下心防,袒露最柔软的衷肠。于是,我们忘了身处何方,忘了时光流逝,也忘了尘世的种种挣扎,万般执念皆可化为一缕轻烟。
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让我们循着墨香小径,踏碎一纸清辉,在字里行间邂逅那倾泻千年的月光。

 WAP版
WAP版
 小程序
小程序 贵港融媒
贵港融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