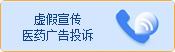玉车于20世纪90年代初入警,现为桂林市公安局某支队政委,是一位公安诗人。他深知,自己生命的根依然在大山深处的洛清江西岸。在诗人的记忆深处,总有些永远挥之不去的熟悉声音和模糊的背影。夜深人静时,隔着茫茫的岁月,那些湮没在时光深处的往事,那些横亘在生命之河的青葱岁月,在朦胧依稀中一一浮现于眼前。因此,他写下《水草深处是故乡》组诗17首。这些回望故乡思乡思亲的乡土恋歌,燃烧着激情,蒸腾着血气,带着诗人的体温,让人一直沉浸在这种略带惊喜的发现和感受中而不能自拔。
回望的乡愁,展现浓浓的亲情乡情和高贵的灵魂。那原汁原味的乡音乡俗乡情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其中有对父母的感恩与怀念,有对故乡山川风物风土人情的真诚歌吟。那一首首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歌,弥散着泥土芬芳,袅袅大山流岚和缕缕炊烟。
显然,爱,是贯穿组诗始终的主旋律,如同一根红线串联起生活的珍珠。而父母之爱,炽烈、深沉、久远,那么纯真,那么动人,洋溢着人性的美,人情的美,折射出超拔的人格精神。
玉车的诗,语言纯粹、干净、凝练、简约,写父母的诗不置一词评价,由读者自己作出判断。《父亲的山坡》《一根木头》《老井》等都是写父亲的作品。父亲在诗人心中是一座丰碑,是一座巍峨雄浑的山坡,他对子女的影响,主要是精神感召和人生引领。如今,劳碌一生的父亲在金鸡岭“长眠在茂密的松林里”,“漫山遍野的松木,了却了一个木匠的心愿”。事实上,父亲虽已离去,却永远没有离开,只是出门远行,他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他伟岸的身躯就像漫山遍野的松木,挺立在金鸡岭上。
《一根木头》写父亲的为人匠心,他的一生如同木头般朴素实诚。父亲敬业,技艺超群,声名远播。“一根原木在他手里被整得没有脾气/方条有大小,木板有薄厚/组合成不同的家具,最后成了器/是的,他做的家具都成了器/包括我的兄弟姐妹,姐姐弟弟妹妹。”这段描写,前部分实写,评价父亲是技艺超群的好木匠。诗的后两句是虚写,潜台词是:父亲不仅是一位好木匠,更是一位好父亲,他通过言传身教,把儿女们培养成人打造成器。后两句诗,幽默风趣,语言有弹性,富有张力。看似突兀,有些莫名其妙,却别出心裁逸出新意,简直是神来之笔。
与父亲粗线条的勾勒不同,对母亲的描写更真切细腻、生动传神。诗人在诗中通过许多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描写,从不同角度刻画母亲,使一位仁慈温婉、勤劳达观、隐忍坚强的母亲形象雕塑般跃然纸上。《老井》写儿时跟随父母去挑水的往事,展现他们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母亲温婉含蓄,遇事适时进行润物细无声的点化,可谓春风化雨。“小时候,我跟着母亲去挑水/打上来的水只有半桶/母亲笑着说:做人不能半桶水。”那时的“我”还小,未必理解“做人不能半桶水”的哲理,却为尔后的人生埋下伏笔。而“与父亲去挑水则不同/他不让我打水,走得飞快/我只能跟在他的身后跑/他硬朗的身板挺得扁担吱吱响”。至此,父亲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性格与母亲温文尔雅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使作品产生强烈的审美反差。
《母亲的河流》描绘了两幅画面,一是显性的人物剪影,母亲亭亭玉立“站在洛清江西岸”“站在夕照的余晖里”定格成永恒。二是隐性的,“我们之间,还有一条或明或暗的脐带/一直牵挂着,能听到你的心跳声/就像母亲河洛清江一样,你在上游/我在下游,水流源源不断”。这动静相宜虚实相生的画面,拓展了审美的时空,诗境顿然宏阔。是的,母爱是人世间最崇高圣洁博大无私的爱,它来自生命本体最本真最原始的冲动。因此,我们纵然浪迹天涯走得再远,都永远走不出母亲的牵挂。
《水草深处是故乡》《母亲的背篓》都是写儿时生活的趣事和母亲隐忍负重的艰辛。前者写“母亲背着我去打捞水草/又背着我与水草回家”,背篓里,不知愁滋味的“我”无法体会生活的磨难与母亲的艰辛,反而感到好玩快乐,因为“水草舞动着身子向我招手/小鱼不停地吐着水泡/仿佛在说:你好,你好!”后者不仅指出背篓的实用性,赶山挖笋瓜果飘香时节,“背篓里装满了果实”,“桃子李子土豆红薯花生”应有尽有。同时指出背篓是诗人和所有大山儿女生命的摇篮。当我读到“母亲出门时背着我,劳作时也背着我”的诗句时,不由得对母亲肃然起敬。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用无悔的青春和一生的辛劳,点亮了自己平凡的岁月,点亮了儿女们心中的一盏盏心灯。
苏轼在《题蓝田烟雨图》中首次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概括王维诗歌的艺术特色。这一评论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中诗画互通理论的经典表述。《童年的大山》是诗画同构的佳作。诗的第二节写道:“天空太小,走在大山中/阳光稀碎丛林里,月亮高悬后山上/山沟溪水淙淙,在我的梦中/千回百转,绕成了一条相思河,依河而上就能找到家”,这是一个远离红尘喧嚣的世外桃源。“阳光稀碎”“月亮孤悬”稍纵即逝,却被敏感的诗人捕捉到,写出月下大山的静穆高远。此诗最绝妙之处在于通过两个传神细节刻画母亲的形象,可谓入木三分,形神兼备。“我每次上学或是赶闹子/母亲总是在我口袋里打一个草结/在书包里藏一根松枝/母亲说了有了草结就不会迷路,点燃满是松油的松枝/照亮回家的路,什么都不怕。”出门打草结就不会迷路未必成真,却寄寓着母亲美好的祈愿和深情。藏松枝是为了“照亮回家的路”。透过这两个细节,母亲把心底里清澈的爱化为熠熠星光。
《走秋》《喊山》写传统的民间习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民俗学的审美价值。前者意欲纵情山水却引出对“三农”问题的忧思。后者在喊山中寄托母亲的理想和深沉的爱。母亲撕心裂肺地喊山,划破了夜空,感天动地,山呼海啸,连沉默的大山也“在风中低声啜泣”。这就是母爱的神奇力量。
《驶过车站》《城市末班车》并非乡土诗。前者告诉我们:人的一生都在路上,人在旅途来去匆匆,“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也没有带走”却依然执着前行,明知寻找的艰难却依然坚持艰难地寻找。因为生命的旅程中总有一些诗意在前方召唤。后者以反讽的笔调写疫情后城市的冷清萧条。夜晚的城市末班车,“车厢空空如也”只有我一个乘客。车过处,大街空荡无人,商店门可罗雀。一种彻骨的悲凉力透纸背,渗透人的整个灵魂。

 WAP版
WAP版
 小程序
小程序 贵港融媒
贵港融媒